儒家遇上法兰西:四百多年前的文明交流初探
17一18世纪,于欧亚大陆的东端,矗立着其势力达到鼎盛时期的大清王朝,在康乾盛世期间,儒家文化得以复兴和发展,儒家经典文献得以被重新考证、汇辑、整理和出版,中国文化史上的巨大里程碑工程《四库全书》得以问世(1772一)。
虽然在此期间也出现了文字狱之类不尽人意的事件,但此时毕竟是开创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兴旺发达的局面。
在欧亚大陆的另一极,欧洲第一王国法兰西处在以“朕即国家”自居的“太阳王”路易十四(1638一1715年)统治前后。
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中,将路易十四比定为古罗马的奥古斯都(Augustus,公元前63一公元14年)大帝。路易十四的心腹权臣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1619一1683年)于1664年开始创建东印度公司,从而开通了与东方(特别是与印度和中国)的交流;
他创办了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1663年)、法国科学院(1666年)和皇家建筑学院(1671年),特别是创办了法兰西罗马学院(法国四大海外学院中的第一所,其余三所依次是法兰西雅典学院、法兰西开罗学院和法兰西远东学院)、专修东方语言的法国青年语言学院和巴黎天文台。
世界上的首部《百科全书》——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一1784年)主编的《百科全书》也在这段时期问世,成了传播诸多学科的综合知识、抨击教会权利和国家反动势力、宣传科学和文化思想的一大阵地,并从此彻底改变了出版物的性质与形式,创立了百科全书派这个崭新的学派。

那么在欧亚大陆的两极,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明与以天主教文化为代表的法兰西文明之间,曾发生过什么样的交流、影响和互动呢?中国儒教文化是怎样在法国传播并施加影响的呢?
法国20世纪下半叶的大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一1979年)于其名篇《中欧最早的哲学交流》一文中指出,这种交流对于双方来说,仅为一种粗浅的试探,但它们却具有深邃的后果与影响,丰富了古大陆两端的文明。本文试就中国儒家文化在法国的传播与影响,略作钩沉。
中国儒家文化向欧洲的传播
中国儒家文化于17一18世纪向法国传播的媒介,应归功于入华耶稣会士们的书简、著述与译作。
我们知道,入华耶稣会士们根据利玛窦制订的“适应中国文化”的策略,从事了大量有关中国科学和文化的研究工作。
我们基本上可以说,他们在这一阶段,于传教中是失败的,在文化交流方面却功不可没。
即使在文化传播领域,他们在向欧洲介绍中国儒家文化方面,要比向中国介绍西方文化方面的成绩更大。
16一18世纪,中国儒家文化的西传以及中国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施加影响的媒介,固然有商贾、游客和使节,但最重要者仍应首推入华传教士们。
自16世纪起,随着地理大发现,西方殖民列强纷纷东来,传教士也就应运而生了。在来华的基督教-天主教诸修会中,除了耶稣会之外还有方济各会、遣使会、多明我会、冉森派、奥古斯定会、巴黎外方传教会、新教诸会,等等。
法国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大史学家圣·西门(Saint-Simon,1706一1825年)于其《回忆录》中,在1788年之下写道:“在有关中国祭祖和尊孔的礼仪问题上,近期所爆发的争论已经是乱哄哄的了。耶稣会士们允许他们的新教徒尊孔祭祖,而巴黎外方传教会却严禁如此行事……已经有人写了整整的几部历史著作了”。
当时在法国确实出版大量有关这场中国礼仪之争的著述和译著,这场争论震撼了整个法国和欧陆。
它事实上仅仅是由于发现不同文明,而在欧洲造成的动荡,也是欧洲对直到当时所坚持的特有文明之动摇的表现形式。
同在1700年,培尔于其《历史批评辞典》中指出:“今天,整个欧洲都响起了传教士们的争执声。
传教士们在欧洲互相指责,教廷枢机处、巴黎大学、王公和作家们都在此问题上不停地活动并作出了百种举措。非常奇怪的是,传教士们的分裂、他们的争执及其互相吞噬,却使他们取得了值得他们吹嘘的成绩与进展”。
这就是说,在欧洲爆发的中国礼仪之争,反而促进欧洲形成了一股热衷于谈论中国的强大“中国热”风潮,从而促进了中国儒家文化在欧洲的传播。
实际上,中国礼仪之争的要害在于传教区是否允许已接受基督教归化的中国人,在不伤害基督教正统的前提下,实施作为儒家文化之特征的尊孔祭祖的礼仪;是否可以将基督徒们的“Dieu”比定为儒家学派的“上帝”或“天”;是否能以“天主”(“天主”无疑是一个起源于佛教的名称)之名而祈祷之。这也是欧洲人在与儒家文化交流中发生的撞击。
欧洲最早的中国儒学和理学概念,出现在最早入华的耶稣会士罗明坚和利玛窦的著作中。
罗明坚(Michel Ruggieri,1543一1607年)是1579年在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字复初。他是利玛窦的先驱,是第一个用中文发表天主教教理书的人,即1584年于广州付梓的《圣教实录》。

他也是第一个将儒家基本经典《四书》译成拉丁文的西洋人。
他本人虽为意大利人,但其著作后来主要是在法国流行。罗
明坚第1次向欧洲人介绍了Luzi(儒子或儒士),称他们为一类“圣人”。
这可能是欧洲有关儒学的第一种印象。利玛窦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于1615年由金尼阁用拉丁文文本刊行于世,1616年便出版法文版,随后于1617年和1618年再版。
法国人通过此书,了解到了有关中国儒学的更多真实情况。因为该书于第1卷第10章中就明确提到:“儒教是中国所固有的,并且是国内最古老的一种。中国人以儒学治国,存在着大量儒家经典文献,远比其他教派更为著名”。
“儒学是目前被普遍信仰的学说”。
他认为儒士宇宙观中的某些思想,是“今天流行的观念”。
此外,利玛窦还可能研究过理学宇宙观,因为他于1604年致耶稣会会长的一封书简中,曾明确地提起“太极”和“理”的观念。
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1559—1655年)是利玛窦在中国传教区的继承人,系1597年往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字精华。
他一生中有58年是在中国度过的,直至客死于华夏大地为止。
他于1624年左右撰成一部《论中国宗教的某些问题》,但由于受中国礼仪之争毒化气氛之影响,它直到1676年才由西班牙入华多明我会士闵明我(Dominico Navarette)用西班牙文本在马德里发表,刊载于其论战性巨著《历史研究》中。
此书在长时间内,仅限于在传教士们的狭窄圈子中流传。
该书的法文版于1701年在巴黎出版,由巴黎外方传教会的西赛(de Cicé)主教自西班牙文译出,从而使法国读者大众更加广泛地了解了龙华民的著作。
此书后来还出版过葡萄牙文译本。
它是欧洲出版的第一部有关中国儒家文化,特别是有关被欧洲人称为“新儒学”之理学的论著。
这本小书也成了18世纪欧洲人士对儒家文化了解和理解的宝贵源泉之一。
它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其出版也颇具历史意义。
作者于其书中指出,中国儒家文化完全是无神论文化,绝不是宗教文化。
正是这本书,才启发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s,1638一1715年)产生灵感,写成了一本《一位基督教哲学家与一名中国哲学家的对话》,开创了中西文化“对话”体裁著作之先河。
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2一1693年)是比利时入华耶稣会士,于1656年到达中国的江西。

他与意大利入华耶稣会士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1625一1696年)、荷兰人鲁日满(Fianqois Rougemont,1624—1676年)以及奥地利入华耶稣会士恩理格(Christian Herdtricht,1624一1684年)联袂,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拉丁文本的《中国的哲学家孔夫子》一书。
这几位入华耶稣会士都在华居住过30年左右。此书还带有一个中文书名《西文四书直解》。
其中有100多页篇幅的绪论,全面介绍了孔子与中国儒家文化。
其中的《孔子传》,疑出自殷铎泽神父之大手笔。
此外便是《大学》《中庸》和《论语》的拉丁文译本。译文系由这一批耶稣会士们译于1660年左右。
《绪论》是柏应理神父在教案期间,于1667年被囚禁在广州牢狱中写成的。
因为在当时广州监狱中关押着从北京和中国其他各地放逐到此的18名耶稣会士和4名其他修会的传教士,而且有关中国礼仪和汉语名词之争,也正是在那里展开的。
出版该书的目的,旨在把孔子描述成了一位全面的世俗伦理学家,断定他的伦理准则和自然神学统治着整个中华帝国,从而支持耶稣会士们于近期间归化整个中国的希望。
它也证明在华耶稣会士们直接介入了欧洲有关中国儒教文化与礼仪的那场旷日持久的大辩论。
此书既深入论述了孔子本人的学说,又介绍了晚期的宋明理学,特别是程氏兄弟、周敦颐、邵雍、张载、朱熹以及明人的《性理大全》一书。
事实上,《中国的哲学家孔夫子》是一部为利玛窦适应中国儒家文化政策辩护的书。
此书在向欧洲,特别是在向法国传播中国儒教文化的历史上,可以说是一座里程碑。
马若瑟(Joseph Henry-Marie de Prémare,l666一1736年)神父是法国入华耶稣会士,1698年往华,在华度过近40年后,逝世于澳门。
西方第一个汉学讲座的创始人雷慕沙曾讲过:“在入华传教士中,于中国文学造诣最深者,当首推马若瑟与宋君荣二神父。
此二人之中国学问,非当时之同辈与其他欧洲人所能及”[1](P256)。
马若瑟研究中国儒家经典,是为了从中寻找中国最古老的传说,特别是《诗经》中的隐喻,以证明中国创造形象文字和编辑经书之前,就已早知天主,从而有利于其布教事业。
他将许多中国儒家典籍邮寄给当时法国皇家文库的傅尔蒙(Etienne Fouirnontt),如《十三经》和明人的《元人百种曲》(《元曲选》)。
伏尔蒙的《中国孤儿》,正是根据马若瑟翻译的纪君祥所著《赵氏孤儿》而改编的。
马若瑟还用法文翻译了不少儒家经典并撰写了许多有关儒家文化的法文论著,以向法国介绍和传播中国的这种居统治地位的文化。
如其法文译本《六书析义》1卷、《前书经时代与中国神话之探源》、《中国语言志略》(1728年)、《书经》选择、《诗经》8篇译本和《经书解说绪论》。
此外,他寄回法国的大量书简中,也都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儒家文化。
刘应(Claude de Visdelou,1656一1737年)是法国入华耶稣会士。
他一生中曾译著过不少有关中国儒家文化的作品。如《中国哲学家之宗教史》、《礼记》多篇译本、《书经》拉丁文译文6卷、《中庸》拉丁文译本、拉丁文《中国历史》6卷、《中国人之礼仪与祭祀》和《汉文<四书>年代考》等,这些也是入华传教士们向欧洲传播儒家文化的重要一环。
冯秉正(Moyriac de Mailla,1669一1748年)是法国入华耶稣会士,1703年来华,45年之后逝世于北京。他以6年的功夫,以朱熹的《通鉴纲目》的译著为底本,编写了巨著《中国通史》,于1737年寄至巴黎,但一直等到其死后才在1777一1785年间;分12卷出版。
从该书530名预订人名单中,我们便可以看到法国18世纪“中国儒学文化热”高潮中的地区和人员阶层划分,也可以看到中国儒家文化在法国的传播概况。
在已经考证清楚的474人中,巴黎326人,波尔多48人,里昂29人;军人85人(22.79%)、神职人员69名(18.05%)、法官43人(11.53%)、自由职业者42名(11.26%)金融人士41名(10.99%)、政府行政官吏30名(8.04%)、女贵族24名(6.43%)[2](P83—123)。
钱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1718一1793年)神父是法国入华耶稣会士。

他自1750年入华,1751年晋京入宫,在北京生活42年和在皇宫中生活25年之后,当他获悉路易十六在法国大革命中被处死的消息后,因悲愤而突发中风暴卒。
钱德明神父撰写了不少向欧洲介绍中国儒家文化的著述。
如《孔子传》,1784年写于北京,其中广泛地使用了孔子的《论语》《家语》以及《史记·世家》《阙里志》,此外还有《圣门礼乐统》《四书人物别传》等载《中国杂纂》第12卷;
《孔子传大事略志》,附24幅图像,出版于1788年前后;
《孔子诸大弟子传略》,1784—1785年撰于北京,内附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和子路传,载《中国杂纂》第13卷;
《中国历代名贤传》,多取材于马端临之《文献通考》,连载于《中国杂纂》第3、5、8和10卷,其中主要介绍了某些儒生并配有图像;
《中国兵法》的法文译注本,载《中国杂纂》第7卷,主要包括《孙吴司马穰苴兵法》的法文译注本;
《中国古今音乐篇》和《中国古代的宗教舞蹈》,主要是论述中国儒家礼乐文明的。
特别是他的《由经典古籍证明的中国历史之远古性》一文,载《中国杂纂》第2卷;这本长达300页的重要论著,解释了儒学最早和最基本的内容。
其中特别以:“太极图”的形式,解释了“新儒学”——理学,他称之为“儒学近代形式”。
作者长篇大论地解释了周敦颐所说的“无极而太极”的意义。
钱德明认为,近代理学家们已丧失了《中国的哲学家孔夫子》一书所赋予他们的那种危险和令人烦恼的面貌。因为在他之前的传教士们,都偏受儒家经典的原文,而摒弃理学家们的注疏。
钱德明认为理学家们的思想遭到了粗暴对待,但事实上是他自己并未注意到在自己身边广泛传播的唯物主义思想。
韩国英(Pierre Martial Cibot,1727一1780年)也是法国入华耶稣会士,1759年入华,在华共生活22年,居京逾20载。
他主要是一名动植物学家,但也向欧洲和特别是向法国介绍过中国儒家文化。
他于《中国杂纂》第8—9卷中发表了《中国语言文学论》,详细阐述了中国的《六书》以及儒家的道德、艺术、历史、宗教、文学、社交、风俗习惯等,特别是其中包括《诗经》若干篇的译文。
除了孔子之外,韩国英于其书中还讲到了周敦颐和朱熹,他认为朱熹是中国曾有过的最伟大的天才,酷似法国的培尔(Pierne Gagle,1647一1706年);
周敦颐酷似法国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伽桑狄(Pierre Bassendi,1592一1655年)。
他认为周敦颐的“理气”学说要大大优于毕达哥拉斯(Pythagore)的对数、卡利斯特拉特(Callistrate)的质量论、德漠克利特(Démocrite)的宇宙原子论、泰勒斯(Thales)的“水是万物基础”论、笛卡儿(Descartes)的三种实体论、伊壁鸿鲁(Epicure)的原子说、莱比布茨(Leibnitz)的单子论。
他的这些译介与比较,对于儒家文化在法国的传播,也起了不容忽略的作用。
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一1743年)是一位从未到过中国的法国耶稣会士。
他自1735年起,推出了4卷本的《中华帝国全志》,其内容全部是入华耶稣会士们寄去的书简和著述。
当然也由杜赫德作过增删、改写和其他编辑加工工作。当时,中国儒学和理学的形象,在欧洲甚为微妙。如他于这套丛书第3卷中发表的《论中国当代文士的教派》,则是上文提到的《中国的哲学家孔夫子》的编译文。
另一篇《中国程氏哲学家对世界起源与现状的观点》,系由法国入华耶稣会士殷弘绪(Francois-Xavi-erd’Entrccolles,1662一1741年)译自汉文的。
这一套文集中,有关儒学和理学的著述相当多。再加上它已被先后译作英、德和俄文本,所以它流传更广和影响更大。
雷慕沙(Abel Rémusat,1788一1832年)虽然主要活动于19世纪上半叶,但他本人的经历就是入华耶稣会士们的著述影响的结果。
他于1815年1月16日,在法兰西学院创设了“汉语和鞑靼语-满语语言文学讲座”。
在他逝世后11年时出版的其论文集《亚洲论丛》第5卷中,发表了一篇《论中国哲学》的文章。
在18世纪时就被入华传教士和西方哲圣们捧上了天的中国儒家文化,又被雷慕沙过高地估计了,其玄学理论既模糊又不连贯。
但全面来看,雷慕沙有关儒学的研究未有多大进步,他对道教的评价却频有影响。
郭弼恩(Charles Le Gobien,1653一1708年)虽从未到过中国,但他由于负责入华耶稣会士们寄回法国的书简与著述等档案,故首创《耶稣会士书简集》的事业。
他于1702年在巴黎推出首卷,共出版8卷。
由于当时欧洲形势的需要,郭氏似乎颇为偏爱中国儒家的伦理道德、政府体制、选官制度,经典史籍。
前文已提到,这套书简集为中国儒家文化在欧洲广泛传播并产生深远影响,功不可没。
中国儒家文化在法国的影响
文化传播是文明影响的前提条件。一旦当必需的条件具备,也就是说在文化背景、人员交流、资料积累方面,都作好充分准备时,中国儒家文化对于欧洲,特别是对于16一18世纪的法国之影响,也就会缓慢而又卓有成效地发展起来了。
非常奇怪的是,当时无论是在华传教士们还是欧洲的许多文人学者,他们中有许多人都奉孔子为基督教的先驱,而又将无神论归于了中国学者。
在欧洲和特别是法国,17一18世纪出版的有关中国哲学和宗教的著作铺天盖地。
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也是不同修会的传教士们的主要争论焦点。
它们震撼了整个欧陆,而且既错误复杂又极为激烈。如果说传教士们在许多问题上从不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共识的话,那么法国的文化精英们都利用他们的争论而获取了有关真正儒学的相当完整的知识。
儒家事实上从不企图使用“宗教”的名称,而传教士们或出于基督教布教的需要,或者是出于成见和过分僵硬的宗教原则,始终都持将儒学视为一种宗教。
其原因首先是由于传教士们是在欧洲哲学尚未从神学中彻底摆脱出来的时候到达中国的,当时宗教对于抽象思维的影响尚很强大。
这些传教士们当然不可能设想出一种与他们的宗教大相径庭的思想意识。
由于传教的需要,复以为讨得中国皇帝的欢心,入华耶稣会士们有意地将“儒教”与基督教相提并论。
其他修会的入华传教士们,又嫉妒其耶稣会教友们成了中国宫廷中的高官,所以要不惜一切代价地破坏这种局面。
后者公开声称,他们来华是为了传教而不是要向中国人学习。
他们认为,无论儒家文化好坏与否,都与自己的基督宗教风马牛不相及。
从信仰的观点来看,儒生文士们都是无神论者,这些人执著于本世间的世俗生活,根本不关心“永生”,而且由于祭祀而成为“迷信者”。
这样一来,这种既是“无神论”又是“迷信”的儒家文化,当然要受“上帝使徒”们的抨击。
我们掌握了大批当时有关“中国人的哲学与宗教”这种老生常谈内容的著述,而且大部分都是以拉丁文写成的。
因为拉丁文比法文更适宜翻译某种外国文献,更可以准确地表达儒家经典的本义,它也是17一18世纪学术界和神学界的一种国际通行语言。
法文本属拉丁语系,故法国人比英、德及北欧人能更多地接触和更好地理解中国儒家经典,从而造成了法国成了欧陆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最大的局面。
传教士们撰写了多部有关孔子的拉丁文著作,在书林中占据一席颇为受尊崇之地。
如上文提到的《中国的哲学家孔夫子》即用拉丁文写成。
众所周知,18世纪是个法国世纪,法国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主战场。
当时也用法文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国儒家文化的论著。
17一18世纪法国出版的论述儒家文化著作如此之多,以致于对有关中国的其他内容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忽略,使人误认为中国只有儒学一家哲学家和惟有儒学一门学问。
但他们介绍孔子,在许多情况下,都已面目全非,成了“西化”的孔老夫子。
中国人把孔子视为一名哲学家,而传教士们却奉他为基督教的先驱,甚至还认为他曾预见过耶稣-基督的降生。
我们仅引《中国人的宗教礼仪》[3](P199)一文中的对孔子的描述为例,以说明这种奇谈怪论。
“西方圣人曾认为,孔子曾预言到耶稣-基督。卫匡国神父于其《中国史》中补充说,孔子似乎预见到耶稣-基督降生的秘密,甚至还指出了实现这种降生的年代,即当有人猎杀一只小动物时,让孔子作出了这种预言。据中国人认为,惟有当一名特别圣洁的人出世时,这种吉祥异象才会出现,它可以向整个大地宣布,一种自数世纪以来就许诺的吉祥将会出现。孔子获悉了这只动物的死亡,便两次哀叹般惊呼:‘麒麟曾下令让你出现,当时吾教正走向衰败,你的出现将使我的全部施教都无益了’。由于麒麟是一种很温和的动物,所以它很可能是暗示上帝的羔羊。况且孔子逝世的年代也与救世主降生的年代有关——尽管要早478年”。
儒家文化与基督教的这种所谓相似性,是由卫匡国神父人为地确立的。
但它不会不使耶稣会士们感到高兴。对于中国文明抱消极态度的雷诺多(Renaudot)教士摒弃了这种荒廖的论点,因为孔子确实从未曾预言过耶稣-基督的降生。
雷诺多的用意,是出自他对中国文明的轻蔑,卫匡国的行为则是为其传教事业服务。
对于中国人来说,孔子遗憾的麒麟之死亡只具有象征意义。
中国传说中认为这种动物具有一种神奇的本领,因为它是动物界中的最聪明者。
孔子本人既博学又具有崇高的品德,却无法使诸侯们理解和实行其理论。
麒麟是动物中最聪明者,但人类却并不重视它的降临并蔑视它。
这就是传教士们杜撰类似故事的本意。传教士们很可能是受唐代韩愈有关麒麟与圣贤关系的论述之启发,才持如此之怪论。
卫匡国当然知道,中国人的麒麟与基督徒的羔羊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但他与其教友们故意歪曲儒学,以便在儒学与基督教之间找到一个共同点。
方济各会士和多明我会士们,出于对耶稣会士们在华活动之成就的嫉妒,也在儒家文化问题发动了攻击。
多明我会士让·德巴兹(Jean de Paz)这样阐述过中国人的尊孔行为:“世人会在我们入华教友们的记述中发现,一名新受归化的教徒,于某一天面对数位不信基督人士而抗议说,他只能像对孔子一样行师徒之礼,而不是像对神(上帝)一样崇拜之。中国人听到这通言论后便忍俊不住地对他说:‘您是否认为我们中有任何人会对孔子这样崇拜呢?我们清楚地知道孔子也是如同我们一样的人。如果我们尊孔,那完全是由于他留传给我们的学说,而使我们如同师徒一般地尊敬他’。同一批教士还介绍说,如果文士之列的某名基督徒不认为应依俗向孔子行礼,那么高官显贵们就会指责他欺师背祖,而不是认为他很少有宗教虔诚心和成为不信基督者”[4](P201—202)。
“我们还应对此略作诠释,中国那些不信基督教的学者们都普遍宣扬无神论,不承认未感觉到的任何实物和道德。中国人完全如同撒都该教徒们那样,既不接受天使,也不承认魔鬼。然而,他们坚信逝世已久的孔子之灵魂既不能给他们带来好处,也从不冀希望从他那里捞到任何好处”。
这大概就是传教士们对“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理解了。
在有关孔子的问题上,耶稣会士们又提出了另一种内容:“孔夫子鼓动其弟子们从天、畏天和事天,如同爱己一样爱其近邻,要克己,非礼勿听、非礼勿语、非礼勿行。更加引人注目的是,他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5]
这一段文字同样也出现在《论中国人的宗教》中了。
作者还讲一步补充说:“在阅读到这一种如此美好伦理和一种应尽义务的如此卓越的典范记述后,谁还会不相信孔子是基督徒,并曾在耶稣-基督的学校中受过教育呢?我们应特别注意作为上天之礼物的这种正直性格,而人类后来都从这种正直性格上堕落了。当然,一名基督徒也不可能表现得更好了。”
通过阅读这些引文,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到,传教士们在有关孔子伦理的看法上是一致的。
但耶稣会士们当时都认为,伦理取决于宗教。
多明我会士们却证明,中国人的伦理独立于宗教。他们对于耶稣会士们的指责,却产生了出人预料的效果。
法国的思想家们本来都倾向于世俗伦理,由此而形成了百科全书派学者们的思想,他们广泛地接受各种知识、信息和资料。由此又产生了一种奇怪现象,由于耶稣会士们的崇拜而遭到歪曲的中国儒学,受到了其对手—多明我会士和方济各会士们的揭露,后者却取得了最后胜利。
耶稣会士们却最终被认为受到了其本质为无神论的儒学所“归化”,所以他们于1742年受到了教皇的绝罚。
17一18世纪时,法国的大哲学家们如同繁星灿烂一般,成了启蒙时代的娇子。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均在不同程度上受过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
培尔是法国18世纪的异端哲学家,著名《历史批评辞典》的编写者、启蒙思想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
他通过入华耶稣会士柏应理的著作而获得了有关中国儒释道三教的知识,特别是熟悉了中国儒学文化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
培尔是出于反对路易十四的偏执而开始关心中国的,由对基督教的成见而转向无神论。
在欧陆爆发的中国“礼仪之争”事件,又为他提供了深入了解中国的契机。
他对于当时似乎被普遍接受的《圣经》中包括了全部人类历史的思想提出了质疑,认为信仰某一尊神并非是道德的标准,以中国儒家的宽容精神来抨击西方基督教社会的狭隘。
他认为像中国儒学文士那样的非基督教道德,并不比基督徒们逊色多少,中国儒学的无神论并不是少数哲学家们的特有专权,而是一种在中国占突出地位的哲学理论。
培尔于其《有关慧星的不同思想》中认为,中国儒家文化的无神论远不会有碍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存在,相反却造成了该国的繁荣昌盛。培尔的全部唯物主义思想受中国儒学的影响很大。
法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神学家和笛卡儿派学家马勒伯朗士受入华耶稣会士中的“异端分子”傅圣泽(Jean-Francois Foue-quet,1665一1714年)的影响,故而对中国又有另一种与众不同的看法。
它虽于其《一名基督教哲学家与一名中国哲学家的对话录》(1708年)中,对他杜撰的那名中国儒学哲学家大肆嘲弄,但他的神学思想明显受中国神话的影响。
他希望从中国人的思想中觅寻归化中国人的手段。
马勒伯朗士极力鼓吹人类的认识均来源于神,而不是出于对事物的直接观感。
此人深受儒学与朱程理学中理气观的影响,力主将朱熹的“理”比定为基督教的上帝,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基神学观。
他反复声称中国的儒家玄学为一种无神论,与斯宾诺莎的唯物论或泛神论具有明显的共同之处。
他的《对话录》实际上是借中国之名而攻击斯宾诺莎的。
所以,中国儒家思想已渗透进当时法国的笛卡儿派神学家和唯心主义学者中了。
法国的独立思想家和怀疑论哲学的鼻祖拉摩特·勒瓦耶(Francois La Mothe Le Vayer,1588一1672年)的《论异教徒们的道德》(1614年),是一篇具有历史批判论特征和怀疑论色彩相当浓厚的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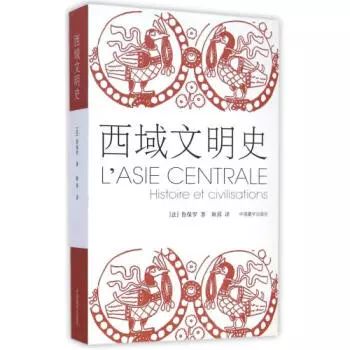
他提出以一种全新的思想来拯救不信基督者,这当然是由于发现中国儒家文化而造成的结果。
他根据中国文人儒士的例证说明,在基督教使徒们未曾到达过的异教徒中,同样也可以获得拯救。
由于中国历史纪年要较《圣经》纪年古老得多,所以他与入华耶稣会士们一样地认为,只有尊崇孔夫子,才能实现归化中国人的目的。
拉摩特·勒瓦耶特别是受到了入华耶稣会士金尼阁所介绍的孔子形象的影响。
此人特别是开创了将孔夫子与苏格拉底进行比较,并认为孔夫子就是中国的苏格拉底之先例。
他尤其赞扬孔夫子的道德与圣性。正是中国的这些儒家文化才使拉摩特·勒瓦耶成为一名不信教的独立思想家和作家。
伏尔泰(Voltaire,1691一1778年)是法国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反对暴政的批判主义哲学家。

他的“中国热”思想主要有三大部分:中国的古老历史、儒学和风俗。伏尔泰终生以“新华派学者”而著称(尽管他晚年更为关心印度),是18世纪法国“中国热”潮流的主要始作俑者。伏尔泰于其《风俗论》(1740一1756年)、《路易十四时代》(1732年)和《哲学辞典》(1764年)等传世名著中,都有专门论述中国的内容。
他幼年求学于耶稣会学院,又与不少入华耶稣会士们保持交往,故深受他们有关中国著述的影响。
伏尔泰为写一部研究世界起源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才开始注意到其历史源流要远远超过《圣经》或越出《圣经》范畴之外的中国的古老历史;
他为了反对当时欧洲的暴政和提倡“开明君主制”,才研究儒教和特别是其中“仁”的观念,因此,而获“欧洲的孔夫子”之雅号;
他为了欧洲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的“反无耻之战”,才注重研究一种东方的异国文化并赞扬中国风俗,他的“中国热”思想完全是为自己的理论服务的。
换言之,他的一整套哲学理论都明显带有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烙印,儒学成了他的哲学体系形成中的一种重要因素。
法国政治经济学家、启蒙思想家和法学家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1689一1755年)是三权(立法、行政和司法)分立制的首创人,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整个西方世界。
他于其《论法的精神》中曾多次论述到中国及其儒家文化,但往往是前后矛盾、互不连贯。
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消除由入华耶稣会士们造成中国儒家文化社会的形象。
他通过入华耶稣会士们的著述而了解中国儒家文化,也深受与其他会友们反目的傅圣泽游说的影响。

孟德斯鸠以西方政府的标准而认为中国拥有一种专制政府,但却又根据其所谓“气候理论”而认为中国人温顺驯服,保持淳朴风俗,不受豪华和富贵的腐蚀。
他赞扬中国政府执法严厉,认为要治理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必须使用“法的精神”。
他特别欣赏中国的税收政策并积极向法国以及整个欧洲推荐。
他研究了中国的文官政府、明经取仕、御史制度、皇权、政权的稳定性、礼仪和民族同化等问题,认为这一切均有相当大的价值。
孟德斯鸿正是在研究了中国和印度之后,才确定了其政府体制理论。
所以,在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也受到了中国儒家政府体制的影响。
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的先驱、教育家、寂静派和神秘论学者费奈伦(Franc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 Fénélon,1651一1715年)曾对中国儒家的礼仪、教育、皇权和经济做过深入研究。
他于其《死人的对话》(1690年)中,也将孔夫子与苏格拉底做了比较。
由入华耶稣会士们描述的中国政府与费奈伦的理想政府之间具有很大的吻合性,特别是在重农方面,所以,费奈伦研究了中华民族的起源问题,中国的官民和君臣之间的父子般关系后,便确立了其君权思想。
他研究了中国的民众福利问题,从而加强了其重农主义倾向。
在他的《泰雷马克历险记》(1690年)以及论教育的著作中,更明显地带有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痕迹。
当然,费奈伦更多地则是想在西方而不是在中国找到改革法国政治的模式,故而又对中国持批评态度。
18世纪的法国受中国影响最大者莫过于重农学派了。
该学派可以说是历史上的第一个科学的经济学派,它在法国历史上曾经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其代表人物是杜果(Anne-Robert Jacques Turgot,1727一1781年)和魁奈(Frangois Quesnay,1694一1774年)。
他们二人均受到了中国儒家文化的很大影响,是为法国18世纪“中国热”推波助澜的主要学者和政治家。
特别是魁奈出任法国崇拜中国的代表人物蓬巴夫人的家庭医生。
重农派学者越出了当时欧洲人只热衷于研究中国儒家哲学、礼仪、宗教、历史之臼穴,顿生借鉴中国的经济制度来改革欧洲经济之奇想。
魁奈创建了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杜果在出任路易十六财政大臣(1774年8月)时,曾根据中国之榜样试行过财政、行政和政治改革。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儒家文化高度重视农业,历代中国王朝都奉农业为国之根本,以自给自足的农业庄园经济为基础。
入华耶稣会士们有关中国农业的著述甚丰。
他们还特别提及中国皇帝每年都亲扶犁把而躬耕第一趟地,以祈告天地保丰年。
这种记述后来甚至被以绘画形式在欧洲广泛传播,吸引了重农派学者,使他们更加坚信世界第一财源为土地,第一职业为农业,从而在中国找到了他们理想的农业国模式。
故魁奈曾于1758年上谏路易十五国王,要求他仿效中国皇帝的楷模,而于春季亲耕。
魁奈的名著《中华帝国的专制主义》和杜果《关于改革和财富分配的想法》(1766年)均为这方面的代表作。杜果于其书中发表了法国学者们在被入华耶稣会士们遣往法国的高类思(AloyKo)和杨德望(Etienne Yang)回国时,交给他们的中国间题调查提纲(其中有近半数是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
前30条是有关中国农业的,其次15条是有关中国的艺术和工艺的,最后6条是有关自然科学的)。
他们于其社会大构思中颇受中国儒家文化之社会结构的吸引。
魁奈虽对中国儒家政府的专制性持批评态度,但仍认为这是一种理想化政府。
他们均向欧洲推荐中国政府的模式。
尼古拉·弗雷烈(Nicolas Fréret,1688一1747年)是当时法国最关心中国的人文学者,他与法国的人华耶稣会士们的通讯足可以证明这一点。
弗雷烈尤为注重对于中国历史纪年和帝国起源问题的研究,他从1743年起被任命为法国科学院的常务秘书。
法国20世纪下半叶的最大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miéwille,1894一1979年)称他为“最具有好奇心、最认真严肃和最富有自由思想的学者”[6](P450)。
他的人文科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入华耶稣会士们所介绍的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
特别是他利用自己在金石的美文学科学院的领导地位,在该院的刊物、报告会及与海外通讯交流中,都大力促进对中国及其儒学的研究。
由于与宋君荣的通讯,他才得出了中国儒生文士都是无神论者或者是斯宾诺莎那样的泛神论者。
他根据柏应理神父的著作而认为孔夫子具有一种神秘教理,认为儒家风俗是中国最崇高和最受器重的一门科学。
他与傅尔泰(Etienne Founmont,1683一1745年)曾企图利用中国福建人黄嘉略(Arcade Hoang)被入华耶稣会士们携往法国的机会,推荐他出任巴黎国立图书馆馆员并任太阳王的中文翻译。
他们曾共同制订了编写汉语语法书和汉语辞典的计划,并且已完成了相当多的工作。
但由于傅、弗之不和与黄氏于1716年早逝,这些计划均被搁浅或夭折。
弗雷烈和傅尔蒙由此都成了在法国本土上从事中国儒家文化研究的奠基人,而且还将汉学研究纳人到了科学院人文科学的范畴。

法国百科全书派哲学家狄德罗在文学、哲学、伦理学、美学、政治学诸领域中都颇有建树,是法国启蒙时代的科学巨匠。
由于他幼年受业于耶稣会士,故对入华耶稣会士们的著述很感兴趣,深受中国和印度的影响,尤其是在其唯物主义思想方面更为如此。
他曾为其1753年出版的《百科全书》(《科学、艺术和技术萃编》)写过不少有关东方哲学与宗教的条目。
后来,他又积极参与编写雷纳尔(Raynal)主编的《两个印度的哲学和政治史》一书(1772、1774和1781年版)。
这两种著作涉及到了法国18世纪介绍中国的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是开扩有关中国儒家文化的知识和好奇心问题,另一方面是将中国奉为欧洲楷模的合理性问题。
雷纳尔于《两个印度的哲学和政治史》的第2版中只列有《吹捧者论中国现状》一章。
狄德罗对此不甚满足,因而又于该书的第3版中增加了《诽谤者论中国的形象》一节,共分20个问题论述中国。
面对由吹捧者和诽谤者造成的不同中国形象,狄德罗指出:“为了做出决断,则必须等待使那些为人公正、识别力强、精通中国文字和语言的人来往奔走于中国各省间,居住在农村,自由地与各社会阶层的中国人交往的时代,这一切方为可能。”
18世纪时,由于法国的带动,在欧洲大陆出版了一大批形形色色的《百科全书》,甚至形成了一个“百科全书”学派。
1734年出版的德国百科全书性辞书《科学与艺术百科辞典》,于第37卷中发表了一条长达10页的“中国哲学”之条目,实际上是抄袭自布鲁克(Johan Jacob Bmcker)于1742一1744年在莱比锡出版的《批判哲学史》第4卷中的段落。
狄德罗于其《百科全书》中,同样借鉴了布鲁克书,他写道:“每个人都可以根据他所赋予这些词的意义,而分别论述中国儒家文化的有神论或无神论、多神论或偶像崇拜”。
“至于那些希望把中国理学中的‘理’仅仅理解为我们‘上帝’的人,当有人反对他们而说明‘理’之正常功能时,他们就会感到非常尴尬”。
他拒绝中国的近代理学与斯多葛派之间的相似性。
享利·贝尔坦(Henri Bertin,1720一1792年)曾先后任法国警察总监、财务总稽核、国务部长和代理外长之职,也是路易十五时代法国“中国热”的推动者之一,也是重农派学者们的挚大。
他与法国东印度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普瓦尔(Pierre Poivre,1719一1786年)、财正大臣杜果是法国启蒙时代关心中国的三大巨头。法国崇尚中国的代表人物蓬巴杜夫人成了他们的保护人。
贝尔坦长期与入华耶稣会士们保持着通讯关系,希望将中国的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东西均引人法国,特别是要大量借鉴中国儒家文化、礼仪和制度。
《中国杂纂》中的许多书简和著述就是由入华耶稣会士们就这些内容而寄给他们的,冯秉正神父的遗作——12卷本的《中国通史》也是由他资助出版的,在为华人高类思和杨德望起草问题提纲时也得到了他的帮助。政界人物介入“中国热”风潮,更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儒学西渐的发展。
阿尔让侯爵(Marquis d’Argens,1703一1771年)是法国启蒙时代的自由思想家,曾与伏尔泰、培尔、孟德斯鸠这些参与当时“中国热”风潮的一代哲学名流们有交往。
他仿孟德斯鸠的《波斯信札》之模式而写了一部《中国信札》(1739一1740年)。
该信札中利用中国儒家文化的观点,来揭露作为18世纪欧洲君主国之通病的政治与宗教的不宽容性,其中包括对斯宾诺莎的批判。
《中国信札》形成了18世纪初叶的形而上学式研究(培尔、莱布尼茨和马勒伯朗士),与此后数十年那更注重政治学的研究之间承启的过渡桥梁。
阿尔让侯爵似乎被“中国化”了,他极力向欧洲推荐具有尧舜道德的中国君主之楷模,认为欧洲尚缺乏这样的君主。
他正是在中国的影响之下,才批判了基督教的政策和哲学,使他具有了唯物主义史观之萌芽。
他将中国的儒释道三教与法国诸教派进行了比较,批判了欧洲各国的有害教义、不公正的司法机构和行为有劣迹的君主、反犹太的基督教等坏的东西。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中国儒士们的智慧、中国文人的道德和中国儒家哲学的唯物观点等好的方面。
法国于18世纪出版的《异教徒们的哲学史》一书的作者布里尼(Levresque de Burigny)为了探听中国的神学,与曾去请教过培尔和雷诺多并阅读入华耶稣会士们有关中国儒家文化的著作。
他由此而得出了中国儒生士大夫无神论的结论。
他在《论上帝的存在》一书第1章中,一方面声称“上帝的存在已几乎被所有哲学家们证实”;
另一方面也指出“某些民族根本不知道上帝的存在”,甚至是像中国人那样“否认上帝的存在”。
他力图证明中国儒生士大夫信奉无神论,主要是为了证明他那“没有任何一种道德行为不由某些异教徒们实施”的论点。他认为人类的两项义务就是热爱上帝和自己的近邻。
因此,伦理是独立于宗教而存在的。中国儒家伦理注重社会联系与社会伦理准则,绝非是受宗教的启发,而似乎是人性本身所具有的。
布里尼的这种唯物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均来自中国儒家文化。
综上所述,在16一18世纪中国和欧洲间,特别是中法之间的首次文化撞击中,中国文化不但吸收了西学中的先进科学,而且也以自己传统的儒家文化对欧洲施加了广泛影响。
民族永远是互相影响的,科学永远是无国界的,文化永远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参考文献:
[1][法]雷慕沙.亚洲论丛集:第2卷[C].巴黎:巴黎出版公司,1829.
[2][法]米桓夫人.从《中国通史》的订购人看法国18世纪的中国热[M].巴黎:巴黎出版公司,l980.
[3]中国人的宗教礼仪[A].偶像民族中的宗教礼俗和习俗[M].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出版公司,1728.
[4]有关中国人尊孔和祭祖的昔日回忆[M].巴黎:巴黎出版公司,1700.
[5][法]奥系良神父.孔夫子的伦理[M].1688.
[6][法]戴密微.法国汉字研究史[A].戴密微汉学论文集[c].莱敦布里尔:荷兰莱敦布里尔出版社,1973.
Dissemination and Impact of China’s Confucian Culture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y in France
Geng Sheng
(Researelt Instidite of History,China Academy of SocialSciences,Beijing,100732)
Abstract:China’s Confucian culture has not only influenced the Chinese history for 2000 years,and it spread to Europe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y,especially to France,the cultural center of Europe. One of the media was the Christian missionaries in China,the other~French philosophers,scientists and statesmen. China’s Confucian culture exeroised prominent influence on the French culture,on the forming of the French philosophical thinking,on its ethics and state system.
注:本文原载于《齐鲁文化研究》第l辑(2002年),第125—133页。
焦点文化
- 流行与乱象:作为新兴文化现象的剧本杀
2 年 3 月 前
- 知名书法家周慧珺去世 她的字帖影响了一代人
2 年 3 月 前
- 视频剪辑短片将被禁 短视频发展痛点如何破解?
2 年 3 月 前
- 汉学家史景迁去世:幽微处展现中国史深刻
2 年 3 月 前
- 热剧引争议的扇 摇出古代生活绰约风姿
2 年 4 月 前
- 全能学霸!这位清代女科学家的经历有多传奇?
3 年 4 月 前

